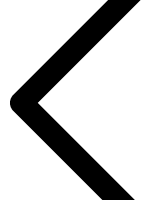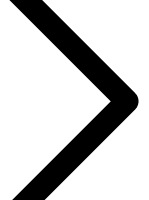摘要:當一場跨年霧霾籠罩中國的很多地方、很多城市,壓力最大的部門是誰?當然是環保部。作為輿論的眾矢之的,他們需要承擔很大的責任,也可能承受了很多的誤解。
每經評論員 傅克友
當一場跨年霧霾籠罩中國的很多地方、很多城市,壓力最大的部門是誰?當然是環保部。作為輿論的眾矢之的,他們需要承擔很大的責任,也可能承受了很多的誤解。
“哪里霧霾最嚴重,我們就去哪里”、“別人是躲著霧霾逃,我們是追著霧霾跑”。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的耳聞目睹,見證了環保部督查組人員的日常寫照——見證了他們在重點城市督查,督查哪些區域,企業;見證了他們現場檢查停限產,查什么,怎么查;見證了面對督查組,地方政府和企業又感受到什么樣的壓力……
通過這樣一場全景式跟蹤,可以澄清公眾對于環保部門的一些誤解——他們不是沒有行動,也不是按部就班、浮光掠影的行動,而是常常在出其不意、雷厲風行地行動,有的放矢的治理也可圈可點,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
但是不難發現,在嚴重的霧霾天氣下,在大面積的環境污染中,環保督查工作仍然困難重重,治理的成效也還是碎片化的,還不能讓公眾真正感到滿意。其中,最大的困難也許就在于,各種利益特別是地方利益的掣肘,讓環保部門還很難真正長出“牙齒”。
在很大程度上,霧霾的治理可以看作一場不同利益之間的博弈,包括長遠的利益與短期的利益、全局的利益與地方的利益、公眾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等的較量。而環保部門、地方政府、污染企業,正代表了利益博弈中的各方。
環保部門當然應該代表長遠、全局和公眾利益。作為首當其沖的第一責任部門,環保部門能不能堅守公眾利益的職責和立場,有法必依、執法必嚴、違法必究,對于霧霾治理最為重要。
的確,霧霾治理是一場持久戰,從根本上來講,它取決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。投資拉動型經濟的增長模式不改變,高能耗、高污染、低附加值的產業結構不調整,霧霾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治理。
但對于短期來說,我們能改善的就是加強監管。公眾的生活環境和身體健康,也不能坐等到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和產業結構改善的那一天。正因為如此,也就更加需要環保部門回歸公共利益本位,更加嚴格地監管和采取更大力度的治理。
無論是從英國還是日本的霧霾治理經驗都可以看到,法律是治理霧霾的利劍,包括環保的完備立法和環保部門的嚴格執法。環保部長陳吉寧日前也指出,治理“小散亂污”企業,是改善空氣污染的有效途徑。
問題在于:那種環保中央部門“督查組”的工作形式,仍然讓人有一種無可奈何的無力感和事倍功半的局促感。
畢竟,最了解當地企業的,還是當地環保部門,而不是環保部。如果地方環保部門不給力,環保部再怎么搞突然襲擊,再怎么疲于奔命,總難免掛一漏萬。一個地級市,大、小企業數量不說上萬,也得有幾千家,怎么能夠全面而又精確打擊?即便有衛星遙感大數據分析系統和網格地圖的“秘密武器”,污染企業仍然可以“道高一尺、魔高一丈”,玩貓和老鼠的躲藏、偽裝游戲。
照理說,地方政府與環保部門、地方環保部門和環保部,應該利益一致,但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,往往讓地方環保部門難以不折不扣地堅守自身的職責。這就是為什么在記者見證的對企業進行檢查執法過程中,地方環保部門雖然也會對違法問題進行處罰、追責,但是往往不會特別嚴厲,而督查組則能做到不給企業“留面子”。
這種利益上的“腸梗阻”,正是環保力量不夠強大的重要根源。當前的地方環保管理體制,導致一些地方政府重發展輕環保、干預環境監測監察執法,環保責任難以落實,有法不依、執法不嚴、違法不究等現象大量存在。
唯有理順治霾利益機制,環保才能真正長出“牙齒”。這就是環保機構垂直管理的重要性所在。2016年9月,中央印發了相關意見,啟動了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,要求在“十三五”末全國省以下環保部門按照新制度運行。其實,與人民群眾對環保執法工作的熱切盼望相比,改革的進程還可以更快一些,改革的力度還可以更大一些。